常闻俗语:"三餐烟火里,藏着人生三味 —— 一曰勤俭立家,二曰康健立身,三曰亲情立心。" 此语浅白,却道尽烟火人间的真谛。我生于幕阜山脉七十年代的小山村,彼时山高路陡,田瘦土薄,一村人靠天吃饭,日子过得像檐下的冰棱,瘦伶伶的,经不得暖阳。人过半百,方知人间其味,在一碗面条里知“五味”杂存。
“一味”是青槐面影里的勤俭味。幼时家贫,是刻在骨头上的记忆。一家七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,粮缸常年见底,一日三餐多是青菜粥,稠时能捞着几粒米,稀时能照见人影。面条这物,在那时的餐桌上,堪比年节的糕点,金贵得很。唯有客至或岁时伏腊,日子要撑些 "体面",母亲才会揭开那只锁着的木箱,舀出半碗麦粉,掺着红薯面擀出几片面来。
五年级那年,四妹呱呱坠地,家里的扁担顿时又沉了几分。父母像两头老黄牛,春种秋收,夏耘冬藏,脊背弯得越来越低,换来的不过是“一年数斗粗粮”。屋后那一亩瘦地,像是老天忘了疼惜,夏收的麦粉凑不满一个布口袋,细数下来不过几十斤。平日若能得一碗面,必是 “汤多面少”,清水里浮着青青菜叶,恰如古诗所云:“青青高槐叶,采掇付中厨。新面来入市,汁滓宛相俱。” 面是细瘦的,菜是水灵的,汤是清浅的,母亲若在汤里滴上三五点油星,那香味能飘满半条巷子 —— 于我而言,便是人间至味了。
那时的我,少不更事,总怨父母吝啬,不能让我把面条吃个尽兴。见邻家孩子偶尔能捧着满满一碗面,嘴角挂着油光,心里便像长了草,直嘀咕:"同为父母,怎的这般不同?" 直到后来看父亲在田里弯腰割麦,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,在裤腰上积成一圈圈盐霜;见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,针脚密得像蛛网,线头舍不得扔,攒着做鞋底 —— 才猛然懂了,那碗里的每一根面,都是父母用 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的辛劳换来的。所谓 “勤俭”,从不是吝啬,而是贫瘠岁月里,父母为一家人撑起的屋檐。
“二味”是煤油灯影里的师恩。1982 年,我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,校址在三十里外的镇上。那时乡间路远,来回要走四个钟头,我怕回家就得跟着父母下地,宁愿在教室啃干红薯,也不愿踏进村口那片田埂。常找借口说 “功课紧”,赖在学校不走。班主任吴老师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,脸上刻着风霜,眼睛却亮得像星子。他大约看出了我的心思,没戳破,只是常在黄昏时站在教室门口喊我:“到我屋里坐坐。”
吴老师住的单身宿舍,不过一间半大,土墙斑驳得像老人的脸,墙角堆着几捆书,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。他总在我进门后,转身就往灶台去。那灶台是泥糊的,一口小铁锅擦得锃亮。只见他抓一把面条撒进沸水,面条在锅里翻涌,像一群受惊的银鱼。等面煮得透了,他捞进粗瓷碗里,堆得老高,又从一个小油罐里舀半勺猪油,慢慢淋在面上,猪油遇热 “滋啦"”一声化开,混着面香漫出来,钻进鼻子里,勾得五脏六腑都动了。
“快吃,凉了就坨了。” 他总这样说,自己则坐在一旁,捧着搪瓷缸子喝水,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。煤油灯的光摇摇晃晃,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高忽低,像幅流动的画。我埋着头吃,面条滑进喉咙,带着猪油的香,烫得舌尖发麻,心里却暖烘烘的。后来才知道,那时粮食定量,吴老师每月的粮票刚够自己吃,他给我煮的每一碗面,都是从自己口粮里省出来的。
有一回我吃得急,呛了半口汤,他赶紧递过毛巾,叹道:“读书是苦事,也得顾着身子。”那语气,像父亲对儿子。那碗面,分量足得很,我吃了满头汗,连汤都喝得精光。放下碗时,见他盯着空碗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柔。后来我才懂,师者之爱,从不在讲台上的高谈阔论,而在这烟火气里的体恤 —— 他用一碗面,给了一个少年对抗贫瘠的底气,也给了我 “发愤识遍天下字” 的动力。
那年秋天,我捧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去谢他,他还是在那间屋里煮了面,说:“路还长,好好走。"”面还是那碗面,香还是那股香,只是我吃出了些别的滋味 —— 那是 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恩情,轻得像一缕烟,却重得能扛住岁月的风雨。
“三味”是肉汤面影里的亲情味。改革开放的风,终于吹进了山坳。父亲是个敢闯的人,那年头村里人还守着生产队的工分,他却揣着几件旧衣裳进了县城,先是在工地搬砖,后来学了修鞋,渐渐有了些积蓄。最让村里人眼热的,是他每隔半月,总能提回一两袋挂面,塑料袋上印着 "富强粉" 三个字,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。
我毕业后分到县城教书,安了家,父母也跟着搬了进来。日子像发面,慢慢膨起来,餐桌再也不必算计着 "汤多面少"。母亲做的面,也变得 "慷慨" 起来。每逢我生日,她必早早在厨房忙活:五花肉切得细细的,熬出一锅肉汤,咕嘟咕嘟冒着泡;面条下得软硬刚好,捞进碗里,浇上肉汤,再卧两个煎蛋,蛋黄流心,蛋白煎得金黄,撒一把葱花,绿生生的,看着就让人欢喜。
她和父亲总坐在对面,看着我吃。我吃得急,她就念叨:“慢些,没人抢。” 我若说 “太香了’,她眼角的皱纹就堆起来,像开了朵花。有一回我问她:“妈,您咋不吃?” 她摆手:“我不爱吃这些,就爱看你吃。” 后来妻子偷偷告诉我,母亲总在我走后,把我剩下的汤拌着饭吃,说 “有儿子的味道”。那时才懂,父母的爱,从不是 “我给你最好的”,而是 “你吃得香,我就满足”。
城里的同学多了,常聚在一起下馆子。酒过三巡,我总要点一碗清汤面,尝一口就皱眉 —— 厨子的手艺再精细,也煮不出吴老师那碗面的暖,更煮不出母亲那碗面的亲。有次请吴老师吃饭,我又抱怨:“还是您当年煮的面好吃。” 老师呷口酒,笑:“此一时彼一时也,境变则味变。” 我梗着脖子反驳:“不是境变,是情变 —— 您那时的面里,有盼头。” 他没再说话,只是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,眼里有光在闪。
“四味”是病中面影里的生死味。2009 年秋,刚开学没几日,肝部突然疼起来,像有只手在里面拧。去县医院检查,医生眉头皱得紧紧的,说 “不好说,去武汉看看吧”。我心里一沉,却没敢告诉任何人。妻子正怀着孕,父母年纪大了,同事们各有各的忙 —— 我揣着那份不安,白天上课,夜里疼得睡不着,就啃两片去痛片。
身体一天天瘦下去,从前能吃两大碗面,如今半碗都咽不下。怕妻子察觉,总把剩下的面倒进垃圾桶,倒时心里像刀割,那可是母亲亲手做的面啊。疼得厉害时,我就想: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,未出世的孩子怎么办?父母谁来养?吴老师的面,母亲的面,还没来得及好好报答呢。
九月廿九那天,天还没亮,我揣着攒的钱,搭上去武汉的班车。同济医院的人挤得像赶集,挂号、化验、做 CT,一折腾就到了傍晚。结果没出来,我在医院门口徘徊,秋风刮得脸生疼,小灵通突然响了,是母亲的声音,带着些沙哑:“今儿是你生日,我炖了肉汤,擀了面,等你来吃呢。”
我喉头一紧,忙说:“妈,我在武汉出差,回來就去。” 她在那头絮絮叨叨:“你最近瘦得脱了形,别总在外头吃,油大,对胃不好......” 我 “嗯嗯’地应着,挂了电话,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。我竟忘了自己的生日!若能在家吃碗母亲的面,哪怕真有什么事,也值了。
街角有个小吃摊,我走过去,声音发颤:“老板,来碗挂面,加俩煎蛋。”面很快端上来,清汤寡水,煎蛋焦了边。我拿起筷子,一口面含在嘴里,咸的、烫的、苦的,混着眼泪咽下去。吃到最后,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,心里却空落落的 ——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后一碗面了吧。
第二天凌晨四点,我就去排队,总算挂上了肝内胆专家的号。方教授看了我的片子,翻了翻我的眼睑,又让我伸舌头,忽然笑了:“小问题,脂肪肝里长了个囊肿,开点药吃半个月,顶多留个小结节。” 我愣了半晌,才反应过来,眼泪又下来了,这次是热的,烫得脸颊发麻。
回了家,我把前前后后告诉父母,母亲抱着我哭,说 "吓死娘了",父亲红着眼眶,一个劲抽烟。那天晚上,母亲煮了一大锅清汤面,用茶油炒了葱花,说 "清淡些,养身子"。一家人围着桌子吃,面条在碗里冒着热气,父亲吃着吃着,突然说:"以后别总下馆子了,家里的面,吃着踏实。" 我点点头,眼泪掉进面汤里,溅起小小的涟漪。那碗面,吃出了劫后余生的甜,也吃出了 "平安二字值千金" 的真。
“五味”是空灶冷锅里的思念味。2020 年的春天,新冠疫情像场突如其来的雪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家里一下子就空了。厨房的灶台再也没有准时升起的炊烟,那只母亲用了三十年的铁锅,洗得干干净净,挂在墙上,落了层薄灰。妻子学着母亲的样子煮面:先烧开水,再下面条,盖上木锅盖 —— 母亲说过,木锅盖能锁住面香,煮出来的面带着木头的清味。可妻子煮的面,总差了点什么。
有回她端来面,叹着气说:“妈煮的面,到底加了啥?” 我尝了一口,面条软硬度刚好,汤里也撒了葱花,可就是没有母亲做的那种味。后来才明白,母亲的面里,有她站在灶台前的耐心,有她看着我吃时的欢喜,有她一辈子的烟火气 —— 这些,是学不来的。
昨夜做了个梦,梦见老屋的灶台。母亲站在灶膛边,火光照着她的白发,她正手把手教妻子煮面:“水要沸透,面要抖散,盖锅盖时得留条缝......”她的手布满裂痕,像老树皮,却稳稳地握着汤勺,在锅里慢慢搅动。我想喊 “妈”,喉咙却像被堵住,只能看着那团雾气,把她的影子越裹越浓。
今晨醒得早,我走到厨房,烧了壶水。水沸时 “咕嘟咕嘟”响,我下意识地喊:“妈,水开了,能下面了。” 话刚出口,又咽了回去。厨房空荡荡的,只有冷风吹过窗棂,“嗖嗖”地响。我拿起面条,撒进锅里,看着它们在沸水里舒展、变软 —— 就像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,那些以为忘不掉的痛,终究在岁月的烟火里,慢慢化了。
面煮好了,我盛在碗里,学着母亲的样子,撒了把葱花。阳光从窗缝照进来,落在面上,泛着细碎的光。我拿起筷子,慢慢吃着,忽然懂了:母亲从没有离开,她就在这碗面里,在这烟火气里,在我往后的日子里,教我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。
这世间的滋味,大抵都藏在寻常烟火里。一碗面,从青槐叶影里的勤俭,到煤油灯影里的师恩,再到肉汤面影里的亲情,最后落进空灶冷锅的思念里 —— 终究让我明白:所谓人生,不过是在三餐四季里,慢慢懂得珍惜;在一粥一面里,渐渐学会和解。(黄秀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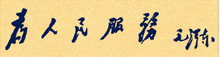




 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
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 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
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